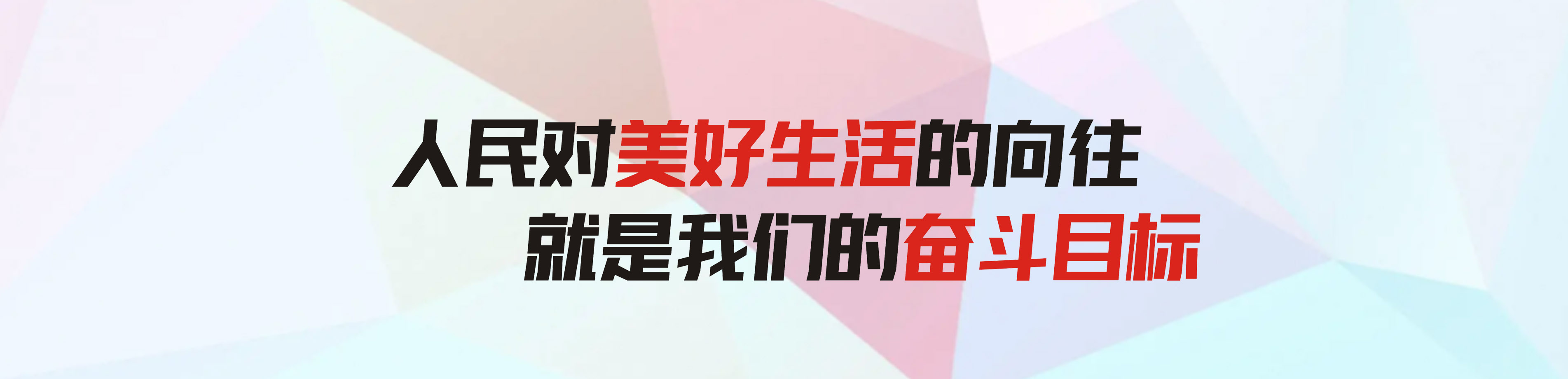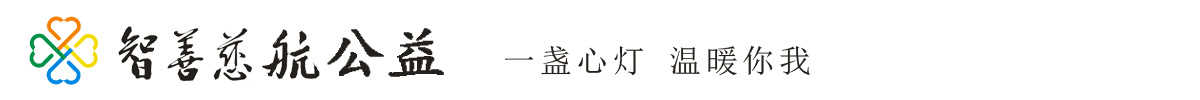
新闻详情News detai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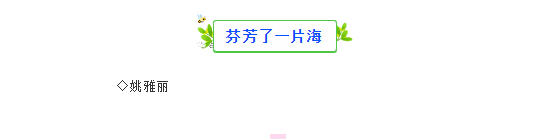
一
我曾在春光四溢的午后,或秋风乍起的清晨,独自一人漫游蟳埔,熟悉得仿若不存在的海洋气息无孔不入。簪花围的姑娘媳妇、阿婆奶奶们也习惯了镜头。她们或淡定地对着镜头微笑,或根本无视掌镜者的存在而自顾开蚵修网。在蟳埔,你很难看到无事闲逛的蟳埔女,簪花与劳作,成了她们的生命标签。
无法说清内心潮湿的原因。每次寻访,都像大海捞针似的,打捞被摧毁得所剩无几的记忆碎片,包括触摸那几幢残破不堪的蚵壳厝,眺望那若隐若现的海丝帆影。时空不可捉摸,每一次的回眸,都像在祭奠自己。
蟳埔村口,隔着丰海路,就是海。丰海路——贯穿城市西东的沿海大通道,把渔村、滩涂、大海隔裂开来,也模糊了人与海浑然一体的原生态画卷,还好尚有海腥味从路旁一溜儿排开的鱼摊里飘出来。泉州靠海,市井十洲人吃海鲜成精,深知船刚靠岸,还没褪去海潮气息的海鲜,最地道,也最为妙不可言。鱼虾蟹们倘若离了海,就算在餐厅酒肆的氧气支撑下依旧活蹦乱跳,但其鲜香已大打折扣。至于那些跨了山水,空运速递到内陆以及北方的海鲜,虽金贵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失去了海的初始记忆。因而丰海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到了蟳埔路段,会减缓行速,摇下车窗,探出一双双眼睛,在一筐筐、一篓篓活色生香的鱼虾蟹上徘徊巡觑。他们有的是吃上了瘾的老主顾,有的是好奇的路人甲。
汽笛奏响凯旋的赞歌,靠港的男人们笑傲江湖,把一船的战利品甩给女人。女人腰挎红色塑料小包,身着斜襟大花衣、阔腿裤,头顶簪花围,笑盈盈地迎接海上冒险者归来。她们的手舞蹈般,幻化出一道道缤纷的虹,一大船几百上千斤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鱼虾转眼间分门别类,一筐筐一箩箩,尘埃落定。
听着涛声长大的蟳埔女,虽然不敢去驾驭茫无边际的浩渺大海,但海对她们永远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她们从不错过任何亲近海的机会。在妻子的鼓动下,夫妇俩驾一条船去讨小海,几十海里,一个潮汛,一天一个来回,收网时也有三两百斤的鲈鱼、小杂鱼、虾姑、虾等。虽让远征者不屑,也比不上男人远洋搏击时大海几千上万斤的慷慨馈赠,但因为有了女人们在浅海撒网、滩涂劳作,让我们享用了更鲜爽、更多样化的海上珍馐。令人隐隐惆怅的是:当年几千平方米的开蚵广场消失了,海港也成了城市腹地。你享用了鱼虾的鲜美,却无法见证风浪的险恶,包括你对海一厢情愿的浪漫臆想。
除去休渔期及天气原因无法出海,蟳埔男人一年出海时间实际也就四五个月。其余时间就做散仙,四处晃荡,打麻将,喝烧酒,享受高高在上的王者待遇。女人累得头晕目眩,倘若不小心抱怨一下,马上遭到一顿抢白:“做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喊什么辛苦?有本事你出海打鱼去!”远征归来的男人永远是渔村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是的,没有他们挑战险恶的大海,哪来的鱼虾满舱?哪来的日子殷实?因为对大海的敬畏,所以敢于征服大海的男人有了神明般的威慑力,在蟳埔男人面前,蟳埔女只能俯首称臣,尽管她们的付出是男人的无数倍。我曾有一回去惠安,和一帮文友乘机动船到一个小岛上。那日启航时海温和恬静,可是傍晚回航时,许是我们一船的喧嚣惊扰了海的梦,它脾气拗上来了。从海的腹腔传出的闷响冲出海平面,海激荡着,怒吼着,扑向我们的机动船,几米高的浪花冲进船舱,把一船二十几个人淋得像刚打捞上来的鱼虾。船激烈颠簸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翻个底朝天。巨大的恐惧像绳索般勒得我几乎窒息。好在船快靠岸时,风平浪止,一颗蹦出的心踉跄回归。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我像获得重生般大喊:“大海太可怕了!”船老大瞥了我一眼,冷笑着说:“在海上谋生,这根本不算什么!”始信那句话——行船讨海三分命!也顿悟在渔村,男人头上顶的是勇士的光环。在男人眼里,女人们是滩涂上的花蛤、海蛎之流。男人只关注大海,女人得承担一切。女人骨子里也把自己看轻。她们低眉顺眼,任劳任怨,像永不疲倦的小蜜蜂;她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收拾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家,煮出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却没有资格和男人一起上桌吃饭,而是拿个碗,装碗饭,蹲旮旯处吃去。“小时候觉得我妈妈很可怜,在家里很没地位!因为妈妈连生两个都是女孩,所以太奶奶对她冷眉冷眼,很不待见。”蟳埔女黄丽泳说起自己的妈妈和太奶奶,一声喟叹,“当年太爷爷抛弃大陆的妻儿,去了海峡对岸,另娶台湾查某,太奶奶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也很可怜。”太奶奶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佯装微笑,伸手接住命运的不公,满头霜雪与耀眼的簪花围交映着生存的坚韧与绚丽。
“我爸爸妈妈感情不错,但爸爸永远觉得太奶奶是对的!”黄丽泳语带伤感 :“妈妈生下我妹妹时,太奶奶简直要发飙了!别人家媳妇坐月子有鱼有肉,我妈妈连饭都吃不饱,太奶奶还到处张罗着要把我妹妹送给别人。”现实就是如此,蟳埔媳妇如果生不出男娃,在家里、村里都得夹着尾巴做人。没有男孩,不但意味着家族无后,更宣告家族与大海的较量自动缴械投降,在蟳埔无立锥之地。难怪老太太对孙媳妇各种刁难,她对曾孙女说得最多的话是:“女孩子能吃饱就好了!”一生吃尽千般苦头的老奶奶把自己的不幸无形地转嫁到自己至亲的女性身上。一代一代的蟳埔女陷于这种因袭而成的意识里,复制粘贴着自己的命运,却浑然不知自己就是自己不幸的炮制者。
男人把家园托付给女人,女人则把梦想交予出海的男人。女人们接纳海的馈赠,也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收入囊中。然而,生活中细如牛毛的琐杂,没完没了的烦恼,果真是弱女子的肩膀能挑得动的吗?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生为男人,或为女人?根本没得选择!生存的本质就是解开接踵而来的一道道难题。没有办法把握的每一次出海,没有办法预料的每一个坎,像一个个魔咒,压在命运之上。唯一可行的是:找一个出口。于是男人纵酒欢歌,肆意挥霍,尽情裸露海的子民的英雄本色。女人则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培植成一朵花,种在泥土里,植入灵肉里。
悲欢被小心隐匿,苦难磨出了珍珠般的光芒,浸红花蕊,组成繁枝琐节招摇于头顶。一朵朵明艳的花,是一群舞蹈的精灵,是光阴的叠加和累积,是等待心上人劈波斩浪而来的腼腆。纵使老了红颜,褶皱里仍荡不去层层闺阁秘密。就像压箱底的红装,抖出来,绵绵密密仍是少女的娇羞。红装、花蕊、甜蜜的梦,在蟳埔,不受时空限制。从牙牙学语的小娇娃,到白发苍苍的老阿婆,都可衣衫明艳,移步生香。耕海耘田的累,养儿育女的苦,操持家务的忙,都化作簪花围的千般光华,万种风情,哪里还有空暇指责命运的层层盘剥?单是头顶那层层叠叠的花,就得投进多少心思?衍生多少甜蜜?骨髻、渔梳、红绳、小把簪、玫瑰、玉兰、含笑、雏菊、粗糠、素馨……每一个季节,都得翘首以盼,采撷含苞待放的美;每一个罅隙,都得穿针引线,裁剪独具一格的韵。
蟳埔女用花做成面罩伪饰自己,她们看上去花一样柔弱,骨子里却有大海一样的硬气。她们貌似活在大海一样嚣张的男人的阴影下,可她们低下头颅时,也正是她们掌控一切时,她们才是蟳埔真正的主人!更确切的表述是:她们是大海真正的主人!男人们以为,天下事除搏击大海之外,其余皆是小事,也是他们所不屑的。所以蟳埔的日常生活,男人是缺席的。他们不管事,不管钱,号称天子实则大权旁落。女人摸黑把一大船的海鲜分拣清楚,或在船上、岸边直接交易,或批发给鱼商,或天蒙蒙亮就挑担进城摆摊设点、沿街叫卖。蟳埔女生来就是做生意的料,她们笑吟吟的,招揽顾客,称重干净利落,算账分毫不差。当她们揣着鼓囊囊的钱包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时,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她呢。柴米油盐、人情往来、生儿育女、垒屋造田,哪一样不是她们在劳筋骨,费心思呢!而当禁海休渔期,或忙碌的空隙,蟳埔的花事与大海的波浪一样,装饰着每一个日子。
蟳埔女与花,彼此相惜。在与命运无止无休的对抗中,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
一朵花开了,一串笑声传来。那是乾坤日月的叮咛,世间万象的萃集。
我是极爱花的人,曾以“采花大盗”的名号行走江湖。但和爱花爱到骨子里的蟳埔女相比,我只能算是过江小卒了。
在蟳埔,花是女人之魂,也是大海之魂。花的坚韧藏在娇柔的外表下,海的凶险藏在波光粼粼里。因了花,海不再只是单调的蓝,村子也不只有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因了花,讨海的日子有了丝绸一样的质感,有了爱情一样的炽热。花,让蟳埔显出与别处的渔村不一样的明媚与深沉。
当然,蟳埔的花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天女散花,而是携着海上丝路的和风而来。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刺桐港,迎来了东非和欧洲许多海丝沿岸国家的商人。当时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掌控泉州的海上贸易,许多阿拉伯商人携家带眷聚居离刺桐港不远的蟳埔渔村。他们带来了阿拉伯风情,也带来解乡愁的素馨花。每当花事纷繁时,素馨花就携着彼岸异香而来,冲淡了海的咸涩。
阿拉伯人不但自己采花、插花,也把庭院里最美的花儿摘赠毗邻而居的蟳埔村民,蟳埔人则回馈以最鲜美的鱼虾。蟳埔人捧着这一朵朵凝聚天地精华,饱含异邦情谊的花儿,不知如何珍重才好。他们知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亵渎。所以把花供奉于高居身体之上的头发,以示无比珍重。
赠花,起先只是在阿拉伯邻居和蟳埔人之间,渐渐地成了蟳埔人之间一种普遍的行为。花,融入蟳埔人的日常,成了蟳埔人的心灵契约。几乎所有重要的时刻,所有美好的情感,都得藉花来表白。蟳埔渔村约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庙宇众多,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节日都是凡人借花献佛,也是神仙们借花漫游人间的时节。加上蟳埔人一生的每一个重要日子:出生、满月、周岁、生日、结婚、生子……都得用花来装扮。连丧事也不拒绝艳色的花,只是花的串数、色彩、质地略有不同。比如不戴鲜花,而以绢花替代,也不能扎红绳,以蓝绳、白绳代之。丧事中,花的串数标识着生者与逝者的亲疏关系。直系亲属一定得戴三串以上,姻亲二串,宗亲一串。在蟳埔人的心目中,花包含着难以言喻的情意,是天地最珍重的赠予,是爱与美的信物,他们把诸多美好的情愫和意象寄寓于花上。渐渐地,赠花演变成一种仪式,继而上升到审美范畴。我没有看到哪一片土地,花如此世俗,又如此神圣。一朵花,珍藏着苍茫时空的记忆,它醒着,或醉着,都是诗。惯于与鱼虾打交道的蟳埔女有一双巧手,她们用红绳或细竹篾,把花儿分类串起来,一圈圈,一排排,有编贝般的璀璨,有珍珠般的晶莹。从天地蕴育,到躬身采撷,素手相赠,直至融进各自的心思。摇曳于蟳埔女头上的花儿芳香了你的鼻息,萦回于你的视线时,已经有了层层叠加的意韵。
蟳埔一年中最盛大的花会当属每年二月初二,顺济宫妈祖天香巡境时。这时,恰是春天繁花似锦的时节,蟳埔渔村吹响了春天的集结号,以盛大的花事招徕天下客。海腥味、脂粉味、百花香糅合成一股属于蟳埔的季候风。沉寂被打破,天空被涂抹成大花脸,大海掀起了七彩浪涛。所有蟳埔女从俗世中抽身,倾尽所能,让春天的花尽情地在头顶妖娆绽放。
珠翠华服面若桃花,笑语盈盈暗香浮动。在一年最潮最炫的花会上,蟳埔女不但把自己装扮得花团锦簇宛若仙姝,还把所有美好的祈愿附丽于簪花围上:红头绳寓意日子红红火火,骨髻末端的金月牙、金蜜蜂说着花好月圆、甜甜蜜蜜,金梳子梳理出描金泼彩的幸福……
彼时的蟳埔便成了一片移动的花海,一首绚丽的诗章——斜襟花衣裳,五彩簪花围,花灯、花篮、花牌、花鼓,延绵数里……因为海神妈祖,蟳埔女戴花蒙上了神圣的意味,她们仿佛脱离了尘俗,在妈祖的牵引下位列仙班。妈祖,融于蟳埔人的生命,又高于他们的生命;妈祖,高踞于蟳埔人的灵魂之上,掌控着蟳埔人的命运。大海的慷慨馈赠与无处不在的凶险让靠海为生的渔民对大海有着令人难以体会的敬畏。海的仁慈,海的深广莫测,发酵成蟳埔人对海神妈祖的虔诚膜拜。蟳埔人携着妈祖出海,他们鱼虾满舱的好日子靠海神成全。所以每年开春开渔,都得以最盛大的庆典来取悦妈祖,感恩妈祖,让妈祖喜笑颜开,也郑重其事地给妈祖布置一年保驾护航的任务。妈祖自是不敢懈怠,时时得穿云望海,眺望调度,摆平风浪,庇佑她的子民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否则,哪来香火鼎盛,庙堂巍峨?哪来玉面金妆,万民膜拜?人与神借助花,通过盛大的仪式来互通心曲,彼此成全。
三
时光倒溯二十年,那时的蟳埔像一块璞玉,阳光照下来反射出的光带着千年前大海的记忆。那时的日子有着潮汛般的安稳,村子里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广场叫蚵埔,二千多名簪花围女子在蚵埔开蚵,一个个鱼贩子或成精的食客就在边上猫着。海腥味、脂粉味、花香味、汗渍味拧成一股蟳埔特有的气流,摇曳着的簪花围延绵成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花海。试想有哪一种劳动场面,如此波澜壮阔?如此摄人心魄?它让人忽略了海的凶险和劳作的艰辛,而把劳作当成一种力与美的展示,一种艺术行为。海的壮阔与花的妩媚,海蛎的鲜肥与收获的喜悦糅合交融。仪式感、庄严感超越了劳作本身,成了对苦难的救赎,对灵魂的引导。它铺就了一条芳香的通道,连接了多维度的空间,天上、人间、过去、现在、未来,花言简意赅地陈述了一切。
早先的蟳埔,家家户户都有几亩薄田,几亩滩涂。女人们在滩涂上种海蛎、海蛏、花蛤,在田地上种农作物,也撒下花籽。薄田瘦地庄稼长得寒碜,花却罕见的好,红的鲜艳,白的素净,黄的妩媚。蚵壳厝前前后后的隙地上,终年有姹紫嫣红的意思。这些花儿,是最为寻常的,不过是好种易活的含笑花、玉兰花、粗糠花、素馨花、雏菊花、九点红……只要有一点阳光,它们就热闹闹地开放,明艳艳地招摇,就像蟳埔渔村里,不需要太多呵护的蟳埔女。世世代代的蟳埔女坚信:这是花神的纤纤玉手洒下甘霖,瘦瘠的土地才有了芬芳与色彩。终年劳作、海风侵袭,蟳埔女过早地褪去了青春的娇柔,粗砺、皲裂的皮肤,艰难沉重得令人难以喘息的生活,因了花而照进了一丝亮光。这亮光,是花仙子对她们苦难的安抚。而今,渔村的地越来越少,可谓寸土寸金,但她们依然把最好的土地让给花。庭院里得堆放渔网、蚵壳,但依然四时有红肥绿瘦。日子有时淬火般烟熏火燎,这时,花像调和阴阳的灵丹妙药一样,让生计柔顺起来,让腥臭的空气有了芳菲,花在蟳埔果真是一种奇妙的平衡。花来唤醒什么?或推开什么呢?蟳埔女人爱花,正如她们深爱着海,包容着自己的男人一样。
花和女人,装点了一座村庄,芬芳了一片海。你单从蟳埔女头顶的花,很难判断她们的年龄和身份。得从头巾、耳饰、衣服的色彩、款式等细节来揣摩。年纪大的阿婆戴老妈头巾、倒钩的老妈丁香,未婚的姑娘则戴圆形耳环,但这些细微的差别都因为簪花围的抢眼而被忽略了。蟳埔女的簪花围飘逸着阿拉伯奇香,大襟衣、阔腿裤则烙上了海上劳作的印记。东方第一大港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船帆,也接纳着异域风情,东西方文化在波光中擦出了火花。这火花,由经一颗颗玲珑妙心,一双双绘春妙手,相袭相承。在蟳埔村,世代相传缝制蟳埔服饰的人毕竟不多。处于泉州市区近郊的蟳埔不是遗世独立的桃花源,现代生活的元素空气般浸入渔村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衣食住行逐渐被同化。细水般流淌的日子里,穿着极具蟳埔色彩服饰的人毕竟不多。时间的流逝,可能会湮没这一切。好在总有一些痴心人,或者说灵魂已被花魂入侵的人,他们手握旧时光,守着旧物、旧制。就像土生土长的蟳埔女黄丽泳,就像坚守着蟳埔服饰、簪花围制作的蟳埔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黄晨。黄丽泳对我说:“我虽然嫁到晋江,但蟳埔仍伸出一双无形的手抓住我。让我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开辟了蟳埔女文创摄影基地,接待来自海内外的游客。我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有更多媒体人、艺术家来关注、传播蟳埔文化,有更多有识之士一起来保护所剩无几的蚵壳厝,让这见证东方第一大港繁华的蟳埔文化传承下去。” 我和黄丽泳聊着聊着,步履已踏入蟳埔女服饰传习所。传习所的主人黄晨放下手中活计,笑着招呼我们。黄晨的父亲当年是蟳埔服饰的名裁缝,黄晨十几岁就跟在父亲身边当小学徒。起初是因为生计,后来就成了一种使命。可是由于穿蟳埔传统服饰的人少,裁缝铺的生意冷清,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甚至多次动了放弃的念头,但心底隐约有一个声音在挽留他,使他放不下手中的布尺、剪刀。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段时间,受各方因素影响,黄师傅的裁缝铺更是门可罗雀,难以维系,他只好转行做服装批发生意。这比起做蟳埔服饰,经济效益自然要好许多,但终究放不下,魂牵梦萦,兜兜转转,还是做回了老本行。坚守,终守得云开见日,迎来传统文化复苏。镌刻海上丝路帆影的蚵壳厝,流溢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簪花围、大襟衫在“一路一带”的欢歌里,像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牵人魂魄。黄师傅也青春重焕,笑颜如花。在他的传习所里,各个年龄、各种款式、各种质地的蟳埔女服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珍贵民俗文化的内涵和嬗变、发展,看到了蟳埔人骨子里的执着和灵魂的芬芳。令我尤为欣喜的是:两个年轻娇美的女孩,正跟着黄师傅学习蟳埔服饰的制作,她们是泉州师院服装设计系的。学现代服饰设计的时尚女孩子,却沉醉于蟳埔文化的芳华里。我看到一拨拨天南地北的游客进进出出,他们艳羡的目光投注于各式各样的蟳埔女手偶和绢制簪花围上。
蟳埔的花和蟳埔的女人,芬芳了一片海,惊艳了时光,惊艳了世人。

编辑:谢奎宗

联系我们Contact us

福建省智善慈航公益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办公室: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东浔美工业区185号
联系电话:0595-22596028
秘书处电话:13559375668
18960295968
微信公众号:智善慈航公益